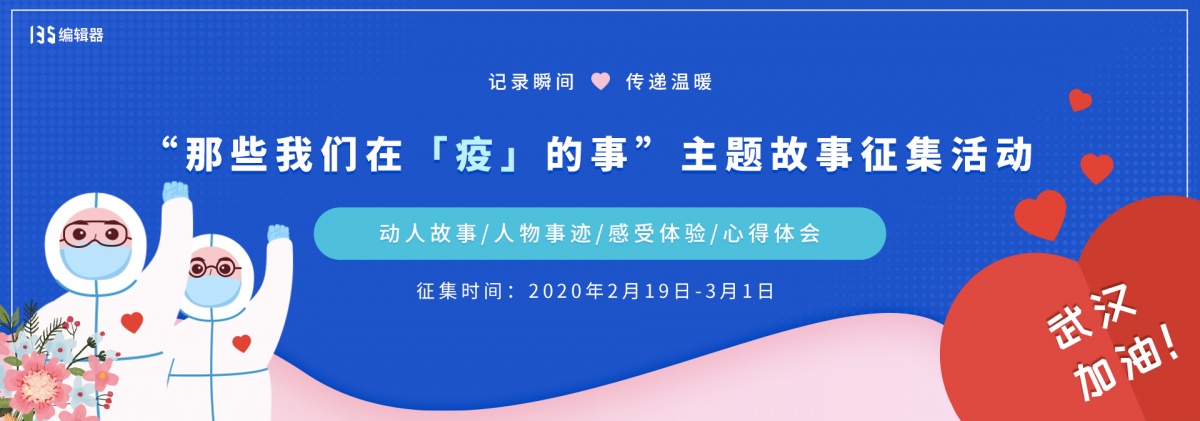時(shí)至今日,我依然不認(rèn)為這場(chǎng)新型冠狀肺炎有其特別性,這也是一直沒有寫關(guān)于這次新冠肺炎相關(guān)文章的原因。請(qǐng)注意,我只是在說這場(chǎng)疫情的普通與平凡,并沒有說它不嚴(yán)重,我當(dāng)然承認(rèn)這次事件的嚴(yán)重性,當(dāng)然看到了無數(shù)鮮活的生命在這場(chǎng)事故中遭受的令人悲痛的罹難,但我們必須承認(rèn)這次疫情與以往任何人類歷史中的災(zāi)難并無不同,它在歷史的長(zhǎng)河中發(fā)生過無數(shù)次,以戰(zhàn)爭(zhēng)、瘟疫、洪水、地震、思想運(yùn)動(dòng)等不同的名字出現(xiàn),而且在未來依然還會(huì)繼續(xù)發(fā)生。
時(shí)至今日,我依然不認(rèn)為這場(chǎng)新型冠狀肺炎有其特別性,這也是一直沒有寫關(guān)于這次新冠肺炎相關(guān)文章的原因。請(qǐng)注意,我只是在說這場(chǎng)疫情的普通與平凡,并沒有說它不嚴(yán)重,我當(dāng)然承認(rèn)這次事件的嚴(yán)重性,當(dāng)然看到了無數(shù)鮮活的生命在這場(chǎng)事故中遭受的令人悲痛的罹難,但我們必須承認(rèn)這次疫情與以往任何人類歷史中的災(zāi)難并無不同,它在歷史的長(zhǎng)河中發(fā)生過無數(shù)次,以戰(zhàn)爭(zhēng)、瘟疫、洪水、地震、思想運(yùn)動(dòng)等不同的名字出現(xiàn),而且在未來依然還會(huì)繼續(xù)發(fā)生。
沒錯(cuò),依然以不同的名字,同樣的形式繼續(xù)發(fā)生,而人們的反應(yīng)和看法也依然會(huì)一如既往。

如果一定要說這次災(zāi)難與以往的差異性,我想唯有一點(diǎn),那就是這場(chǎng)災(zāi)難發(fā)生在如今這個(gè)時(shí)代,發(fā)生在一個(gè)網(wǎng)絡(luò)信息化極度成熟的時(shí)代,這意味著我們?cè)诘谝粫r(shí)間了解到這次疫情情況的同時(shí),也可以聆聽到任何一個(gè)角落對(duì)此發(fā)出的聲音。當(dāng)我們同時(shí)聽到這千千萬萬個(gè)不同聲音時(shí)、當(dāng)所有人以一個(gè)觀察者+參與者的身份存在時(shí),其吊詭性就出現(xiàn)了。
那些溫馴的面容變得猙獰,那些冷靜的心緒變得狂熱,那些平凡的事物變得崇高,那些理智的雙眸變得盲目,那些常識(shí)的認(rèn)知變得顛覆,那些親密的關(guān)系變得遙遠(yuǎn),那些熟悉的規(guī)則變得陌生。
在這一時(shí)刻,這個(gè)世界看似面目全非,其實(shí)卻是本相畢露,那些恐懼、貪婪、自私、狹隘、無知、空洞都一覽無余地暴露在白日之下。

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而言,這里闡述的一些論點(diǎn)是“反社會(huì)”的,某些人看完一定會(huì)勃然大怒,但其實(shí)這些看法并不是什么新鮮開拓性的論點(diǎn),甚至可以說已經(jīng)是老生常談。我并不想對(duì)此作出過多的解釋和辯護(hù),因?yàn)殛U述這些基本性的“常識(shí)”對(duì)于很多具有獨(dú)立思考能力的人來說已經(jīng)是浪費(fèi)時(shí)間,而對(duì)于那些混沌無知的人而言,你說什么他們都不會(huì)接受,因?yàn)樗麄円呀?jīng)喪失了對(duì)新鮮事物的接受力與思辨力,永遠(yuǎn)停留在原始思維。
人們總覺得讀史可以避免重蹈覆轍,但如果歷史讀的夠多的話,就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,因?yàn)閹浊陙磉M(jìn)化的是科技卻不是人性,人性內(nèi)核一旦在遭受到外界沖擊后,自然就會(huì)剝離被文明粉飾的外殼,展現(xiàn)出最原始、最真實(shí)的面目,這也就是歷史總是不斷輪回的原因。如果你去詳細(xì)了解過中外歷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災(zāi)難,無論是十字軍東征、中世紀(jì)黑死病、西班牙流感、切爾諾貝利事件、埃博拉病毒、神戶地震,你都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這次新冠肺炎你所經(jīng)歷的一切都是前人所經(jīng)歷過的,哪怕是在一些虛構(gòu)的作品中,你也可以窺見這類事件的始終。

在這次疫情中,有兩部電影被反復(fù)提及,一個(gè)是韓國(guó)導(dǎo)演金成洙的《流感》,一個(gè)是美國(guó)導(dǎo)演斯蒂文索德伯格的《傳染病》,兩部電影用不同的手法為觀眾呈現(xiàn)出了一場(chǎng)疫情中社會(huì)、國(guó)家、個(gè)人的真實(shí)反應(yīng),舍棄某些經(jīng)過加工的戲劇沖突,你完全可以將這兩部電影當(dāng)做一個(gè)紀(jì)錄片去觀看,這次疫情如今還沒有結(jié)束,但電影已經(jīng)結(jié)束,我甚至惡作劇地猜想會(huì)不會(huì)有某些“先知”會(huì)以電影情節(jié)去預(yù)測(cè)事件的發(fā)展。
《流感》是標(biāo)準(zhǔn)的商業(yè)娛樂片,以災(zāi)難片+驚悚片的題材為我們呈現(xiàn)出一場(chǎng)流感在韓國(guó)引發(fā)的動(dòng)蕩。為了符合災(zāi)難片的敘事節(jié)奏,流感在其中被設(shè)置為極高傳染率與高速爆發(fā)性,感染的人往往很快就不治身亡,韓國(guó)政府為此采取了一些緊急甚至極端的措施進(jìn)行應(yīng)對(duì)。剝離其中某些劇情需要的娛樂因素,你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很多疑惑都可以在電影中得到印證。

在疫情最初,很多人批評(píng)武漢政府對(duì)于疫情的披露不及時(shí),而后武漢市長(zhǎng)周先旺先生在一次采訪中回應(yīng):對(duì)于疫情的通報(bào)要符合《傳染病防治法》,作為政府必須得到授權(quán)后,依法披露,引起民眾對(duì)這一說法的巨大質(zhì)疑。在《流感》中,你可以看到韓國(guó)總理對(duì)于這一事件的態(tài)度,在議員提出要將事件對(duì)外公布時(shí),韓國(guó)總理如此回應(yīng):“人類在危機(jī)面前是無法冷靜的,如果宣布了,人們就鬧翻天了,反而比病毒更加可怕。”
沒錯(cuò),比起流感也許民眾的恐慌會(huì)給這個(gè)社會(huì)造成更大的災(zāi)難。
所以我覺得在大家質(zhì)疑武漢市張周先生對(duì)事件披露是否及時(shí)時(shí),更應(yīng)該思考的是周先生對(duì)疫情披露的時(shí)間點(diǎn)沒有使其造成更大的傷害(這種傷害包括病毒的傳播和恐慌會(huì)引起的動(dòng)蕩)?
當(dāng)然這個(gè)問題不會(huì)有答案,因?yàn)槲覀儧]辦法去證實(shí)另一種可能性,可是往往思考的方式與寬度比答案更有價(jià)值。

對(duì)于傳染病的控制手段,自古以來最有效的就是三種方法:控制傳染源,切斷傳播途徑,保護(hù)易感人群。
武漢封城,無疑采取的是控制傳染源的手段,可是由此又引發(fā)了另一個(gè)問題,對(duì)于武漢市未被感染的人群來說,是不是存在巨大的危險(xiǎn)性?如果隔離措施不當(dāng),會(huì)不會(huì)在武漢市內(nèi)交叉感染造成更多的病患?(這也是日本撤僑官員因?yàn)楦綦x不當(dāng)導(dǎo)致一人染病而自殺的原因。)
那么進(jìn)而又引出了另一個(gè)更為深刻的問題:如果承認(rèn)封城會(huì)對(duì)一定健康的武漢市民造成危險(xiǎn),那么此舉是否有悖倫理?武漢市民是否存在被迫地犧牲小我成全大我?我們由此可以想到那個(gè)著名的道德困境——電車難題:在失控的火車軌道上,你是救一個(gè)人還是救五個(gè)人?人命可否以數(shù)量去衡量?
在《流感》這部電影中,ZF 官員將病毒高發(fā)地盆塘區(qū)進(jìn)行封鎖隔離,設(shè)置治療檢查大本營(yíng)。但單方面推行的隔離措施引起醫(yī)生和民眾異議,醫(yī)生反對(duì)此舉認(rèn)為如果將感染者和可能感染者放在一起的話,感染速度會(huì)急劇上升,感染率百分之五十的病毒會(huì)造成20萬盆塘市民喪生,韓國(guó)總理對(duì)此回答:“如果不采取此舉,則會(huì)造成韓國(guó)人民(5100萬)的百分之五十喪生。”

韓國(guó)總理選擇犧牲一部分盆塘市民來守護(hù)整個(gè)大韓民國(guó),韓國(guó)總統(tǒng)得知此舉時(shí)反問道:“難道盆塘市民就不是大韓民國(guó)的國(guó)民么?”
正如前文所言,這是自古以來的道德困境,注定不會(huì)有一個(gè)所有人都認(rèn)同的答案,前一段時(shí)間引起媒體激烈討論的《奇葩說》議題:“在一場(chǎng)大火中,是救一幅名畫還是救一只貓?”正是對(duì)于電車難題的改編延伸,李誕在節(jié)目中持反方觀點(diǎn),他認(rèn)為應(yīng)該救貓,在其辯論中說過這樣一句話:“正是這些為了一些宏偉的事業(yè)、遠(yuǎn)大的目標(biāo)而犧牲別人的人,頻頻地讓我們這個(gè)世界陷入大火。”
李誕的說法也許在這一事件中并不適用,甚至很多人都會(huì)認(rèn)為對(duì)于封城這一行為完全沒有探討的必要,所謂的探討在嚴(yán)峻的形式面前只是書生式的迂腐和優(yōu)柔寡斷。但持如此說法的人,那只是因?yàn)槟悴皇恰俺侵腥恕保阒皇且砸粋€(gè)局外人的角度去看待問題。我想說的是,對(duì)于這類問題也許永遠(yuǎn)不會(huì)有答案,但對(duì)于這類問題的探討,卻正是人文主義建立的基石,而只有人文主義的建立,“人”才為人。
與《流感》偏重商業(yè)娛樂片不同,《傳染病》則更為嚴(yán)謹(jǐn)、客觀,片方請(qǐng)來了哥倫比亞大學(xué)感染和免疫中心的教授作為電影的醫(yī)學(xué)顧問,學(xué)術(shù)般地為觀眾科普了病毒傳播過程、基本傳染指數(shù)等一系列科學(xué)問題。擅長(zhǎng)群像式拍攝手法的導(dǎo)演斯蒂文索德伯格,在這部電影中更是為我們呈現(xiàn)出了社會(huì)各個(gè)階層、各個(gè)職業(yè)的人物在面對(duì)疫情的真實(shí)反應(yīng),其中有冷酷的政客、前線不幸染病的醫(yī)生、投機(jī)的商人、無人問津的患者...... 千姿百態(tài)的眾生相躍然紙上。

其中有兩個(gè)細(xì)節(jié)特別值得玩味,一是勞倫斯費(fèi)仕伯恩飾演的疾控中心負(fù)責(zé)人奇弗醫(yī)師,得知病毒的高危性后,在公布疫情前夕將消息透露給自己的女朋友讓其盡快逃離芝加哥,而因此遭受到“利用職權(quán)為身邊人謀利”等一系列指控。
這使我想到了李WL醫(yī)生事件,2019年12月31日李WL在意識(shí)到新冠肺炎的嚴(yán)重性時(shí),在武漢大學(xué)臨床04級(jí)班級(jí)群里發(fā)布消息說:“華南海鮮市場(chǎng)確診了7例SARS冠狀病毒”,提醒同為臨床醫(yī)生的同學(xué)“讓家人親人注意防范”。三天后,他因“在互聯(lián)網(wǎng)發(fā)布不實(shí)言論”,而被轄區(qū)派出所提出警示和訓(xùn)誡。2020年2月7日,醫(yī)生李WL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感染,經(jīng)全力搶救無效去世。

至此,全網(wǎng)一片嘩然,指責(zé)武漢市相關(guān)部門未對(duì)其言論有所重視導(dǎo)致了“吹哨人”李文亮醫(yī)生的犧牲及疫情的大面積擴(kuò)散,那張訓(xùn)誡書也將相關(guān)部門永遠(yuǎn)地釘在了恥辱柱上,李文亮醫(yī)生由當(dāng)時(shí)的“造謠者”變?yōu)榱丝删吹挠⑿邸?/span>
但是,在我們緬懷李醫(yī)生的同時(shí),卻有幾個(gè)問題該思考:李文亮醫(yī)生到底是不是造謠者?相關(guān)部門的訓(xùn)誡是否合理?李文亮醫(yī)生到底是不是英雄?
如今看來,李醫(yī)生當(dāng)然不是造謠者,他以一個(gè)專業(yè)醫(yī)師的身份第一時(shí)間對(duì)外發(fā)出了警告。但是試想,如果在另一個(gè)時(shí)空、在一個(gè)病毒存在并在起初就得到有效控制的時(shí)空,李文亮醫(yī)生對(duì)民眾而言還是不是造謠者?

而對(duì)李文亮醫(yī)生的訓(xùn)誡,相關(guān)部門公布的通告如下:“一些網(wǎng)民在不經(jīng)核實(shí)的情況下,在網(wǎng)絡(luò)上公布、轉(zhuǎn)發(fā)不實(shí)信息,造成不良社會(huì)影響。公安機(jī)關(guān)經(jīng)觀察核實(shí),已傳喚8名違法人員,并依法舉行處置懲罰。”
從通告上看,如果是在當(dāng)時(shí)疫情未被權(quán)威部門證實(shí)的情況下看,李醫(yī)生被有關(guān)部門訓(xùn)誡確實(shí)合法,這也是避免社會(huì)秩序造成影響所采取的必要舉措。正如前文所言,在某種情況下,哪怕信息屬實(shí),但民眾恐慌所造成的危害也許會(huì)比病毒更為嚴(yán)重。可是相關(guān)部門的做法雖然合法,但是否合理?對(duì)于一個(gè)專業(yè)醫(yī)師于班級(jí)群聊天所發(fā)出的內(nèi)容,其舉措是否過于敏感、武斷?
而且從通告內(nèi)容中我們可以看出,李文亮醫(yī)生是在“網(wǎng)絡(luò)上發(fā)布不實(shí)信息”,前文有所提及李醫(yī)生發(fā)出警告的群是武漢大學(xué)臨床04級(jí)的班級(jí)群,也就是說是他的私人同學(xué)群。這也引出了第三個(gè)問題,在私人群對(duì)親朋好友發(fā)出警告的李醫(yī)生到底算不算英雄?
那么進(jìn)而又將引出一系列的問題:英雄的定義該是什么?我們?yōu)槭裁葱枰⑿郏拷袷肋€值得英雄出現(xiàn)么?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。

《傳染病》這部電影中另一個(gè)值得玩味的細(xì)節(jié)則是關(guān)于發(fā)國(guó)難財(cái)?shù)氖录玫侣屣椦莸莫?dú)立記者,與藥商勾結(jié)后在其博客上大肆宣揚(yáng)存在病毒特效藥——連翹(一種中草藥制品),導(dǎo)致市面上的連翹被搶購(gòu)一空,甚至在某些藥房引發(fā)暴行。這部神預(yù)言的電影很難不使得我們想到前一段時(shí)間的雙黃連事件,而更巧的是雙黃連口服液的成分中恰好正有連翹。
1月31日晚,人民日?qǐng)?bào)于微博發(fā)表“31日從中國(guó)科學(xué)院上海藥物所獲悉,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”,引發(fā)全國(guó)對(duì)雙黃連口服液的搶購(gòu),甚至雙黃蓮蓉月餅也被搶購(gòu)一空。

在這一事件中我們看到的是政府公信力的缺失與民眾的愚昧。
很難想象這么荒誕的事件竟然源于最權(quán)威的官方媒體——人民日?qǐng)?bào),如果官媒傳遞的信息都無法做到真實(shí)準(zhǔn)確,那么民眾又該靠什么獲取信息、信任又該如何依靠?而且在這樣一個(gè)話語權(quán)被掌控的機(jī)體下,如果官媒的公信力喪失,則會(huì)導(dǎo)致民眾對(duì)一系列媒體、學(xué)術(shù)機(jī)構(gòu)等都喪失信任。
以此觀之,我們是否應(yīng)該重新思考一下新聞自由與新聞道德?

而對(duì)于第二個(gè)問題,民眾真的如此愚昧么?
是的。
在古斯塔夫勒龐貝的《烏合之眾》一書中提出,群體的形成意味著個(gè)性的消失,展現(xiàn)出一致性的低智商、情緒化、盲目性,所有人都屈從于一個(gè)群體性的目標(biāo)和價(jià)值觀,哪怕這個(gè)目標(biāo)再為荒謬。
在這次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,在官媒報(bào)道后,所有人都在議論雙黃連口服液,暗示性在此產(chǎn)生、群體就此形成,原本作為個(gè)人的獨(dú)立意志和理性也隨之喪失,所有人都在以雙黃連口服液為最終目標(biāo),無意識(shí)的人格在此時(shí)起到指導(dǎo)性的作用,進(jìn)而表現(xiàn)出一致性的狂熱、愚昧、沖動(dòng)等特征,鬧劇就隨之發(fā)生了。

《傳染病》中出現(xiàn)了在藥房對(duì)連翹的打砸搶的行為,幸而在雙黃連搶購(gòu)的事件中此類行為并沒有發(fā)生,但不要以此錯(cuò)誤的認(rèn)為本國(guó)國(guó)民具有更高的文明性,在我看來只是僥幸,還記得釣魚島事件中街頭對(duì)日系車、日料店的打砸搶么?
在另一部與疫情相關(guān)的巨著《鼠疫》中,加繆對(duì)人性的愚昧有過另一番表述:“人世間的罪惡幾乎總是由愚昧造成,人如果缺乏教育,好心也可能同惡意一樣造成損害。人有無知和更無知的區(qū)別,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,最令人厭惡的不道德是愚昧無知,沒有遠(yuǎn)見卓識(shí)就不會(huì)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愛。”
我們?cè)谶@次疫情中聽過、見過太多愚昧,雙黃連事件只是滄海一粟。
傳聞?wù)f,這次疫情是武漢實(shí)驗(yàn)室小三上位故意泄露,于是人們開始謾罵權(quán)貴;
傳聞?wù)f,抽煙和煙花爆竹能防止肺炎,于是人們拼命吸煙;
傳聞?wù)f,病毒緣起是武漢人民吃蝙蝠,于是人們開始攻擊武漢人民該遭天譴;
傳聞?wù)f,動(dòng)物可以攜帶病毒,于是相關(guān)社區(qū)、組織便開始捕殺貓狗......

人們?cè)谶@一事件中表現(xiàn)出了空前的無知和狂熱,在其中最令我憤慨竟然是捐款問題,本是善意的捐款在此時(shí)卻淪為了做人的“義務(wù)”和道德的“檢視”,捐款的人高尚,不捐款的人卑劣;捐多的人高風(fēng)亮節(jié),捐少的人厚顏無恥;捐的傾家蕩產(chǎn)的人流芳百世,捐的留有余地的遺臭萬年。
真的是令人瞠目結(jié)舌。
在探討捐款問題之前,我們必須理解另一個(gè)概念,這個(gè)概念叫做“稅收”。稅收是指國(guó)家為了向社會(huì)提供公共產(chǎn)品、滿足社會(huì)共同需要、按照法律的規(guī)定,參與社會(huì)產(chǎn)品的分配、強(qiáng)制、無償取得財(cái)政收入的一種規(guī)范形式。 它是公共財(cái)政的主要來源,其職能主要用于國(guó)防和軍隊(duì)建設(shè)、國(guó)家公務(wù)員工資發(fā)放、道路交通和城市基礎(chǔ)設(shè)施建設(shè)、科學(xué)研究、醫(yī)療衛(wèi)生防疫、文化教育、救災(zāi)賑濟(jì)、環(huán)境保護(hù)等領(lǐng)域。

看到這里我想已經(jīng)不必再過多解釋,所以從嚴(yán)格意義上來講,作為一個(gè)依法納稅的公民,已經(jīng)履行了對(duì)國(guó)家的義務(wù)、已經(jīng)做出了對(duì)救災(zāi)的貢獻(xiàn),完全沒有必要再進(jìn)行捐款。那么捐款是否還有意義?當(dāng)然有,但它只應(yīng)該有一個(gè)意義,那就是善意的表達(dá),對(duì),只是如此,完全不該摻雜其他任何附加價(jià)值,這也就是佛家講究的財(cái)布施。
而且我們必須明白,主動(dòng)表達(dá)善意和被呼吁表達(dá)善意甚至被要求表達(dá)善意是完全兩個(gè)性質(zhì)。可如今我們看到的現(xiàn)狀卻面目全非:某些組織厚顏無恥地募捐、相關(guān)企業(yè)部門對(duì)職工的強(qiáng)捐、民眾對(duì)公眾人物的逼捐等等,捐款已經(jīng)淪為某些人別有用心的工具。
而且對(duì)于捐款這個(gè)問題,還有一個(gè)值得思考的點(diǎn)是,助人為樂和助紂為虐往往只有一線之隔。
從某種角度上看,給災(zāi)區(qū)捐款和給路邊乞丐施舍錢財(cái)是一個(gè)性質(zhì),在《暗訪十年》這本書中,作者針對(duì)乞丐問題寫道:“任何一個(gè)乞丐,沒有加入丐幫組織,是完全不可能在城市乞討的,給乞丐錢,只會(huì)縱容這種好逸惡勞,不勞而獲的思想。那些一直懷有“愛心”,給乞丐錢的“善良”之人,因?yàn)槟銈儯鞘欣锏钠蜇ぴ絹碓蕉啵馐懿缮鄹畹膬和膊粩喑霈F(xiàn)。助紂為虐,與謀財(cái)害命何異。 ”(請(qǐng)注意,這里談的問題是針對(duì)錢款,而并非物資。)
對(duì)于《暗訪十年》作者提出的觀點(diǎn),我們見仁見智。

最后,我想再聊聊這次疫情中的歧視問題與個(gè)體的關(guān)系。
新型冠狀病毒于2月11日被國(guó)際病毒分類委員會(huì)正式命名為“SARS -CoV-2(嚴(yán)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冠狀病毒2型)”,而在此之前,在國(guó)際上僅稱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或中國(guó)冠狀病毒、武漢冠狀病毒。這也曾引起了民眾的熱烈抗議,指責(zé)其叫法存在歧視性。
在我們看到華人脆弱的玻璃心時(shí),也該思考一下個(gè)體定義與歧視的關(guān)系。
我們?cè)诩m結(jié)他國(guó)對(duì)新冠病毒的叫法時(shí),頓時(shí)化身為中華民族,同仇敵愾,可是卻忘了我們前不久還在疫情爆發(fā)時(shí),對(duì)封城前夕出逃的武漢人一片詛咒謾罵;運(yùn)往重慶防控中心的口罩,被大理在中途截獲強(qiáng)行征用;某小區(qū)擔(dān)心病毒傳入,禁止醫(yī)護(hù)人員下班回家......
可能在所有人都人人自危的時(shí)候我們才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,什么才是世間最準(zhǔn)確的存在單位。

在種族中,白種人歧視有色人種;在國(guó)家中,歐美地區(qū)歧視亞非地區(qū);在財(cái)富中,有錢人歧視窮人;在中國(guó)內(nèi),北上廣的人歧視“鄉(xiāng)下人”、南方人歧視北方人、漢族歧視少數(shù)民族、村東頭歧視村西頭、小兒子歧視大女兒....... 我們從人種、洲際、國(guó)家、地域、職業(yè)、財(cái)富、民族、宗族一路走到最后,發(fā)現(xiàn)“種族歧視”以各種變相的方式無所不在。
在己身利益遭受觸犯時(shí),我們總是很容易遺忘不久前我們還堅(jiān)信擁護(hù)的一些事物與概念。如此看來,世間或許根本不存在什么“共同體”,人與世界的關(guān)系只有“我”與“他”之別。
那么,作為人的個(gè)體才是世間最準(zhǔn)確、最真實(shí)的存在。
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認(rèn)為所謂的“集體”、“共同體”、“黨派”、“公司”、“學(xué)校”、“民族”、“國(guó)家”,實(shí)際上都只存在于想象當(dāng)中,在《想象的共同體》一書中對(duì)于這一概念進(jìn)行解釋:“
第一,這個(gè)共同體的成員絕大多數(shù)都是分散的、相互沒有個(gè)人聯(lián)系的,但他們能夠通過各種媒介“想象”出一種把他們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整體;
第二,這個(gè)共同體在空間上是有限的,它一定是有邊界的,因?yàn)樵谒獯嬖谥渌愃频墓餐w,由這個(gè)邊界就產(chǎn)生出“主權(quán)”的概念;
第三,這個(gè)“主權(quán)”的概念是至高無上的,它并非只是狹義的領(lǐng)土主權(quán),而是這個(gè)廣義的共同體作為集體本身就有一種基于想象的至高無上的權(quán)力;
第四,想象的共同體”是一種想象中內(nèi)部“平等的社群。”

有些晦澀?好,我們?cè)賮砜纯从韧郀柡绽凇段磥砗?jiǎn)史》中提出的對(duì)想象共同體的判斷方法:
“怎么知道某個(gè)實(shí)體是否真實(shí)?只要問問自己它是否會(huì)感覺痛苦。放火燒了宙斯的神廟宙斯不會(huì)感覺痛苦;歐元貶值,歐元不會(huì)感覺痛苦;國(guó)家在戰(zhàn)爭(zhēng)中遭到擊敗,國(guó)家也不會(huì)真正感覺到痛苦。然而,如果士兵在戰(zhàn)爭(zhēng)中受傷,他確實(shí)會(huì)感覺痛苦;饑餓的農(nóng)民沒有食物可吃,會(huì)感覺痛苦。這些實(shí)體,則屬于真實(shí)。”
是的,很多你一直秉持、堅(jiān)信的概念和事物,或許一點(diǎn)意義也沒有。
如果看懂了這個(gè)概念,則相應(yīng)的會(huì)引發(fā)出很多問題:
民族主義有沒有合理性和正當(dāng)性?
個(gè)人出于他們無法控制的原因而“生為某人”,就一定要終身背負(fù)相應(yīng)的責(zé)任和義務(wù)嗎?
它應(yīng)該規(guī)范、要求其成員無條件的服從并在某些境地作出犧牲嗎?
在虛構(gòu)想象中高談更為扯淡的榮耀、崇高、光輝、偉大、神圣..... 是不是滑天下之大稽?
挺虛無,挺有意思。

聊到這里也差不多了,這篇文章陸陸續(xù)續(xù)寫了很久,但到最后依然并不完善,因?yàn)橄胝f的東西實(shí)在是太多了,但很多東西又沒辦法詳盡、準(zhǔn)確地表達(dá)出來(原諒我筆法的拙劣),其實(shí)我知道寫這樣一篇文章除了再次梳理一下自己的想法,一點(diǎn)意義也沒有,作為七千字的長(zhǎng)文,相信是沒有幾個(gè)人有耐心一直看到最后的,但沒有關(guān)系,因緣際會(huì),隨遇而安。
曾經(jīng)和一個(gè)傳說中很牛逼的茶者聊天,我問了她很多關(guān)于普洱茶的問題,有些問題可能過于刁鉆,類似于“矛和盾”的問題,但并非存心刁難,確實(shí)是我心中的真實(shí)疑惑。她當(dāng)時(shí)神色有些不悅,有些問題未予回答,最后以一個(gè)長(zhǎng)輩教訓(xùn)晚輩的姿態(tài)對(duì)我說,我的知識(shí)體系太混亂了,應(yīng)該看一點(diǎn)大部頭的書籍,應(yīng)該建立“Basic Knowledge”——基礎(chǔ)知識(shí)框架(是的,當(dāng)時(shí)她說的就是英文)。
其后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“Basic Knowledge”?前不久一個(gè)朋友給了我答案,這也是我這篇文章通篇都在闡述的一個(gè)概念——開放性。
沒錯(cuò),開放性——對(duì)一件陌生事物或概念的接受度、思辨力、寬容性。